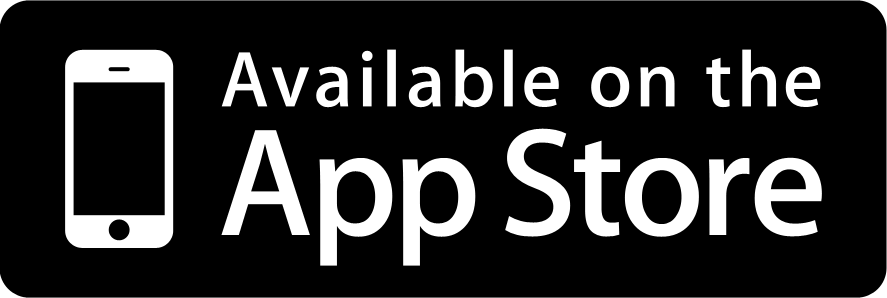iWeekly
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,颁给了艾丝特·杜芙若(Esther Duflo)、阿巴希·巴纳吉(Abhijit Vinayak Banerjee)和迈克尔•克雷默(Michael Kremer)。诺贝尔委员会表示:“他们的实验研究方法现在完全主导了发展经济学,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在实践中战胜贫困的能力。”杜芙若和巴纳吉是历史上首对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奖的夫妻,二十多年前两人在麻省理工相遇,杜芙若在巴纳吉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课程。两人都对发展中国家和穷人感兴趣,于2003年建立了“贫困行动实验室”。他们拒绝泛泛的概括和公式化的思维,在全球进行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,花费无数时间观察和学习世界上穷人的日常,最重要的是实际倾听穷人的意见。他们的工作首先在于,改变人们理解贫困的方式,消除偏见,将穷人视为“具有所有复杂性和丰富性”的人。《商业周刊》将他们形容为“务实的反叛者”,认为他们“引领了一场评估革命,将行为经济学应用于全球发展”。